劍圖薦書(shū)
【劍圖薦書(shū)】《人世間》:平凡人應(yīng)該怎樣度過(guò)這一生

在一檔熱播綜藝?yán)铮?jīng)提到這樣的問(wèn)題,“如果終其一生只是個(gè)平凡人,你后悔嗎?”
似乎大多數(shù)人對(duì)于“平凡”總是心有不甘。
那要有多少平米的房,多豪華的車,有什么樣的社會(huì)地位,才能稱作“不平凡”呢?
無(wú)論過(guò)去、現(xiàn)在,還是將來(lái),平凡而普通的人們,永遠(yuǎn)是一個(gè)國(guó)家的絕大多數(shù)人。
做一個(gè)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喪嗎?并不是,平凡不等同于失敗,事實(shí)上,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平凡的人之間。
央視開(kāi)年大劇《人世間》最能打動(dòng)觀眾的地方就是這種平凡人家的煙火氣,在那個(gè)特殊的年代,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平凡的、普通的人們,為了生存而奔波、奮斗,年復(fù)一年,雖談不上感天動(dòng)地,但這就是平實(shí)而真切的百姓日常生活。
每個(gè)人都希望能夠比平凡的大多數(shù)不平凡那么一點(diǎn),如何追求更好的生活,改變?nèi)松兔\(yùn),在劇中早已告訴我們答案。
擔(dān)當(dāng)
《人世間》刻畫(huà)的周氏一家,父親周志剛是新中國(guó)第一代建筑工人,早年,周志剛咬牙借了點(diǎn)錢蓋了間土坯房,一家五口人就這樣在北方城市的城鄉(xiāng)接合部光字片安了家。
周志剛為人忠厚老實(shí)、深明大義,在周家三個(gè)孩子,不論是后來(lái)成長(zhǎng)為國(guó)家干部的周秉義、大學(xué)教授周蓉還是扎根社會(huì)底層的周秉昆身上,我們都能看見(jiàn)良好的家庭教養(yǎng)。
周秉義品學(xué)兼優(yōu),有理想有抱負(fù),“上山下鄉(xiāng)”運(yùn)動(dòng)一開(kāi)始,他就第一批響應(yīng)號(hào)召離開(kāi)了城市。
周蓉是新時(shí)代知識(shí)女性的代表,她樂(lè)觀豁達(dá)、向往自由,為了追求愛(ài)情,不遠(yuǎn)千里追隨詩(shī)人馮化成去了貴州山區(qū)當(dāng)老師。
周秉昆不如哥哥姐姐那樣出色,但他重情重義,扎根社會(huì)底層,從木材廠到醬油廠再到出版社,在普通的崗位上兢兢業(yè)業(yè),盡職盡責(zé)地努力工作。
后來(lái),周志剛?cè)ネ拇ㄖг€建設(shè),二十余年里,一家人很少能團(tuán)聚。
1986年,60多歲的周志剛終于退休了,回到了他熱愛(ài)的光字片。退休后的他也沒(méi)閑著,這位從“大三線”退休的老建筑工人,似乎把光字片當(dāng)成了“小三線”,獨(dú)自承擔(dān)起了改良光字片的神圣使命。
在春夏秋三季,人們經(jīng)常見(jiàn)到他在抹墻,既抹自家的墻,也抹街坊鄰居家臨街的墻。人們也常見(jiàn)他修路,鏟鏟這兒,墊墊那兒。
有路過(guò)的人心疼他,勸他道,“一條小破街,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?”
他卻說(shuō):“弄弄總歸好點(diǎn)兒,反正閑著也是閑著。”
梁曉聲說(shuō),“那個(gè)時(shí)期的中國(guó)人,有一種‘有一分熱,發(fā)十分光’的精神,我想這種精神不只是在焦裕祿這種黨員干部身上,而是在很普通的農(nóng)民、工人、科技知識(shí)分子,甚至相當(dāng)多的父親、母親身上全部體現(xiàn)了。”
即使前路艱辛,他們也沒(méi)有放棄對(duì)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,互幫互助,共同進(jìn)步。
讀書(shū)
中國(guó),是一個(gè)有著5000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(guó),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優(yōu)秀的傳統(tǒng)文化,是我們?nèi)≈槐M、用之不竭的思想寶庫(kù)。習(xí)近平總書(shū)記高度重視文化自信,他指出“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。”
周家大哥周秉義在“上山下鄉(xiāng)”前,總是躲在家中看書(shū),他和郝冬梅總能找到以前不曾讀過(guò)的“禁書(shū)”,周蓉和男友蔡曉光也是他倆地下讀書(shū)活動(dòng)的積極參與者,幾個(gè)人在周家拉上窗簾,聽(tīng)秉義讀《戰(zhàn)爭(zhēng)與和平》《紅與黑》等,有時(shí)還會(huì)一起討論。
母親雖然不識(shí)字,但每當(dāng)孩子們?cè)谖堇镒x書(shū)時(shí),她卻從不反對(duì)。
自己的子女自己了解,他們絕不會(huì)把壞書(shū)當(dāng)好書(shū)讀。
秉義下鄉(xiāng)前一天,指著一只舊木箱告訴秉昆里邊裝的全是書(shū)。“那些書(shū)在以后的中國(guó),在一個(gè)不短的時(shí)期內(nèi)將難以再見(jiàn)到,很寶貴。我希望咱們周家的后人還能幸運(yùn)地讀到那些書(shū)。一個(gè)人來(lái)到世界上,一輩子沒(méi)讀到過(guò)這些書(shū)是有遺憾的。”
恢復(fù)高考后,周秉義和周蓉相繼考入北京大學(xué),引得光字片的街坊議論紛紛,“人家的兒女可都趕上了好時(shí)代!”“在都認(rèn)為讀書(shū)沒(méi)用的年頭里,咱們的兒女怎么就沒(méi)長(zhǎng)那前后眼呢!”
讀書(shū)最大的好處就在這里。
知識(shí)改變命運(yùn),讀書(shū)是這個(gè)年代打破階層固化最高效的渠道。也許在財(cái)富和人脈方面,你無(wú)法與出生在上層社會(huì)的孩子相比,但在讀書(shū)這件事上,大家是平等的。這樣當(dāng)機(jī)會(huì)出現(xiàn)的時(shí)候,你才可能緊緊抓住。
善良
懂事的哥哥姐姐們下鄉(xiāng)了,留城的小兒女,在不知不覺(jué)地成熟著。
年三十的時(shí)候,秉昆蹬著借來(lái)的平板車帶周母去大眾浴池洗澡。
秉昆洗得快,比約定時(shí)間提前二十分鐘就出來(lái)了,便在外邊等著母親。
突然浴池內(nèi)亂哄哄地涌出些人來(lái),仔細(xì)一看,是一個(gè)男服務(wù)員背著個(gè)叫疼不止的老大爺。
原來(lái)是老爺子穿衣服時(shí),不慎滑倒,站不起來(lái)了,估計(jì)摔斷了一條腿。
那年月沒(méi)有出租車,公共汽車也不是隨時(shí)可見(jiàn)。
秉昆就主動(dòng)說(shuō)自己愿意將老爺子送往醫(yī)院,讓浴池的服務(wù)員將老爺子放在平板車上。
為了避免老爺子的雙腳在路上凍傷,秉昆脫下棉襖將他的腳包嚴(yán)實(shí)了,自己則穿著單薄的秋衣蹬車去醫(yī)院。
那時(shí)的秉昆并不知道,老爺子叫馬守常,是軍事工程學(xué)院的副院長(zhǎng),而他的老伴,正是秉昆所在的醬油廠的支部書(shū)記。
老兩口對(duì)秉昆當(dāng)年的幫助一直記在心里,對(duì)秉昆提供了不少幫助。
后來(lái)在談到筆下的眾多人物時(shí),梁曉聲曾說(shuō),“在極特殊的年代,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況下,青年的一些人,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線,并在做人的底線上盡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標(biāo)和心靈標(biāo)桿的層級(jí)——這才是我后來(lái)一再寫(xiě)‘知青小說(shuō)’的原因。”
所以,善良、正直、富有同情心等美好品質(zhì)一直是梁曉聲作品中人物的主要特征,這個(gè)社會(huì)需要“好人文化”的存在,希望能多一些真善美、少一些假丑惡。
幾十年來(lái),梁曉聲都堅(jiān)持著書(shū)寫(xiě)普通人的生活。而與一些將目光集中在平民的劣根性的作家不同,梁曉聲更關(guān)注的是普通人在艱苦的社會(huì)環(huán)境中所表現(xiàn)出的閃光點(diǎn)。
第十屆茅盾文學(xué)獎(jiǎng)?lì)C獎(jiǎng)辭寫(xiě)道:“在《人世間》中,梁曉聲講述了一代人在偉大歷史進(jìn)程中的奮斗、成長(zhǎng)和相濡以沫的溫情,塑造了有情有義、堅(jiān)韌擔(dān)當(dāng)、善良正直的中國(guó)人形象群體,具有時(shí)代的、生活的和心靈的史詩(shī)品質(zhì)。他堅(jiān)持和光大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傳統(tǒng),重申理想主義價(jià)值,氣象正大而情感深沉,顯示了審美與歷史的統(tǒng)一、藝術(shù)性與人民性的統(tǒng)一。”
《人世間》已經(jīng)大結(jié)局了,但我們的人生并沒(méi)有完結(jié),普通人的生活還在繼續(xù),愿每個(gè)人都能像片尾曲唱的那樣,像種子一樣,一生向陽(yáng)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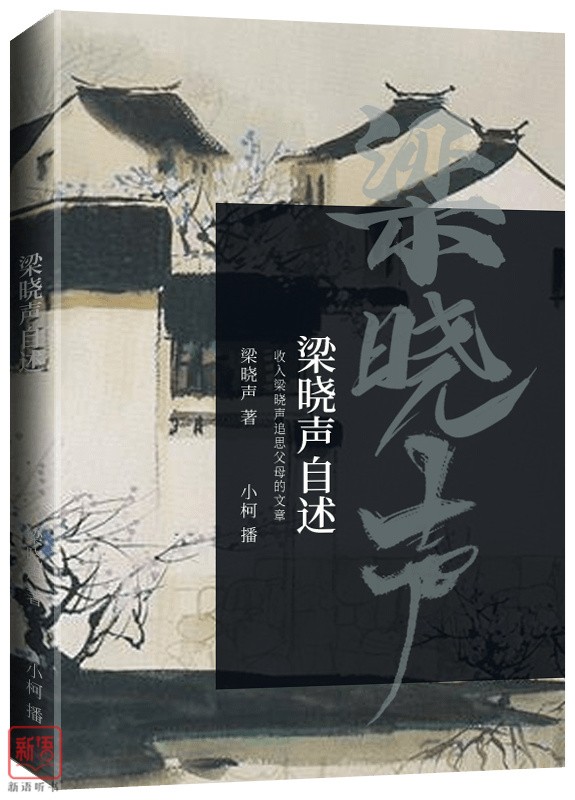

作者:梁曉聲
播音:小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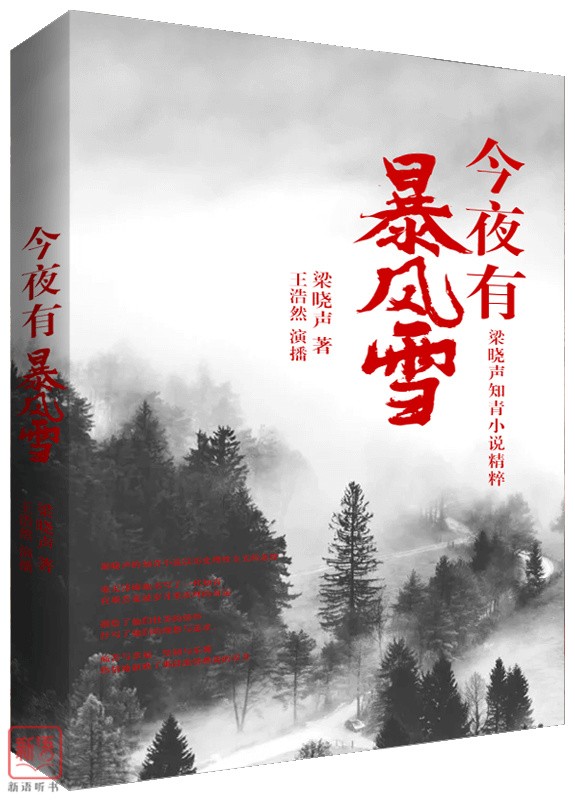

作者:梁曉聲
播音:王浩然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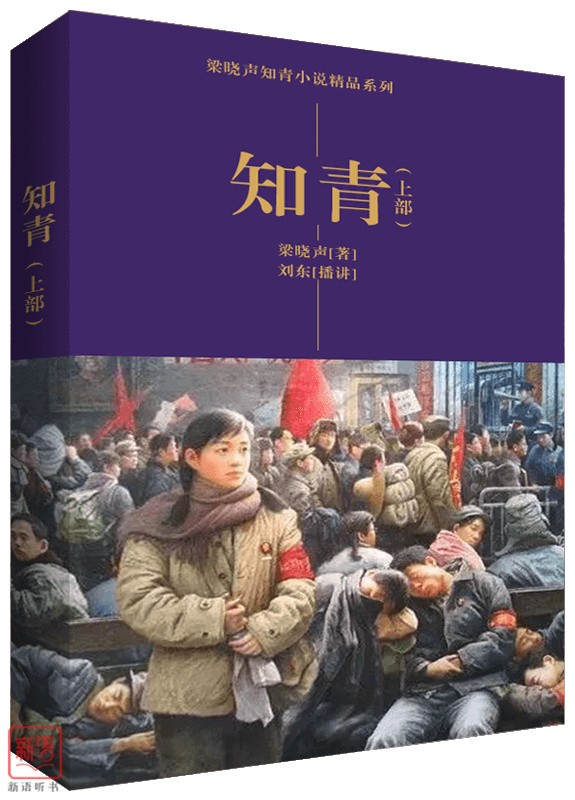

作者:梁曉聲
播音:劉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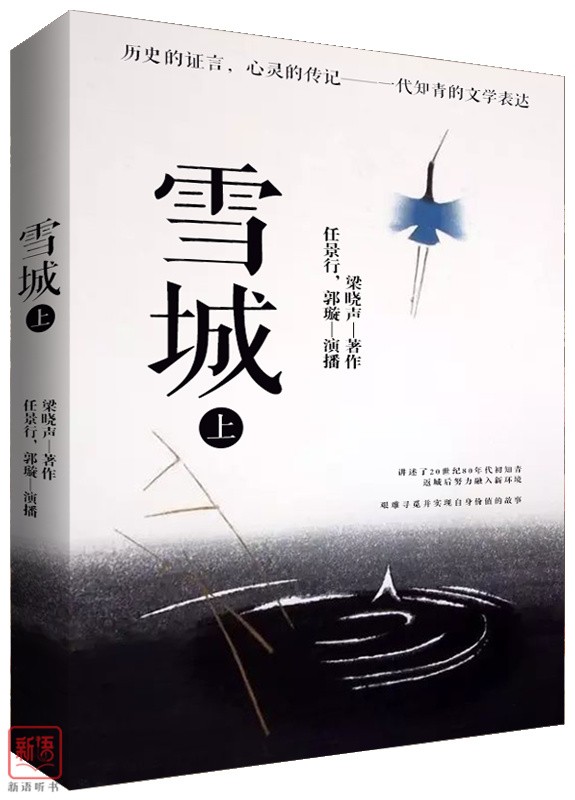

作者:梁曉聲
播音:任景行,郭璇